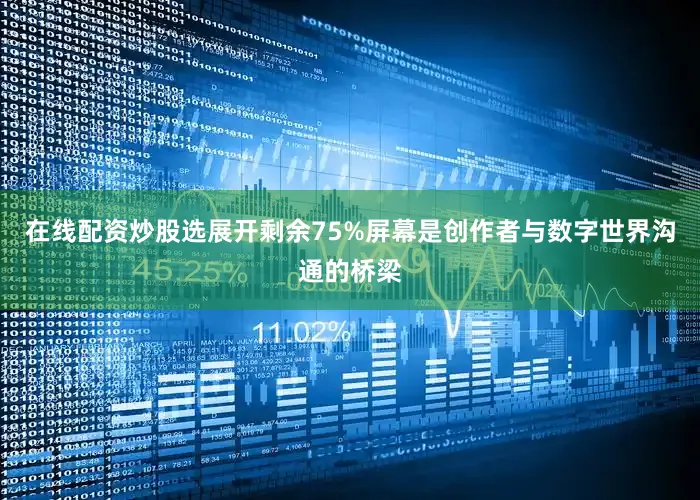《史记》中记载,姬昌继位时已经成为“西伯”,即西土诸侯的首领。根据文献记载,“公季(季历)卒,子昌立,是为西伯”。然而,当时的崇侯虎却因谗言称:“西伯积善累德,诸侯皆向之,将不利于帝。”通过这些记载推测,姬昌获得“西伯”之称的时间可能是在季历去世后,但问题在于,史书记载季历仅被文丁封为“牧师”,很快就被文丁囚禁并杀害。在商人的眼中,周族当时仍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游牧部族,因此他们仅能封季历为“牧师”。那么,姬昌的“西伯”之称到底从何而来?
商人与周人的甲骨文有着不同的认知,对“西伯”之称的理解也有较大差异。从商朝甲骨文中的记载来看,“伯”并非严格的爵位称号,反而代表了一种地方性部落的首领。在殷墟甲骨文中,确实存在不少部落或势力称为“伯”,但这些并非指称其为“爵位”,而是指代非殷商宗室的部族首领。这一发现令许多学者重新审视了甲骨文中的“伯”字。实际上,甲骨文中从未出现“西伯”或“南伯”这样的职务称号。如果“西伯”是一个真实的职务,应该出现在甲骨文中,但它并未被发现。至于是否有可能是商王特别为姬昌设置了“西伯”这一职位,这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。
展开剩余68%商朝的宗室首领一般称为“侯”,这一称谓来源于“侯”字的原始含义,“侯”本指的是哨所的士兵或侦察兵,后来成为了管理一个地区的领袖。在关中地区,商朝曾有一个名为崇国的地方,其首领被称为“崇侯虎”。由此可见,商朝的“侯”字并非单纯的爵位,而带有侦察和卫戍的职能。若按照这种理解,西伯即使是西方诸侯之长,亦不应由姬昌来管理崇国,显然这不符合逻辑。
关于姬昌的职务,我们从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中找到了更多线索。正常情况下,与先王或天帝沟通,是商王特有的权力,其他人无法染指。如果其他地方的领袖也能与天帝沟通,商王的地位无疑会受到威胁。然而,在周原的甲骨文中,却有一些卜辞暗示姬昌也曾试图与天帝沟通,这可能表明他已经有了反商的思想。这些卜辞通常用微雕技巧刻写,细节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。更为关键的是,这些甲骨文中提到的姬昌职务并非“西伯”,而是“周方伯”。
在一些较为完整的卜辞中,记录了姬昌被纣王册封的情况,部分卜辞内容为:“贞:王其拜佑大甲,册周方伯?”这显然表明,姬昌当时被册封为“周方伯”,而非“西伯”。这些卜辞中显示,纣王将姬昌视为一个西方小邦的领袖,而非一个拥有更高权力的“西伯”。因此,史书将姬昌称为“西伯”,显然是后人根据周朝时期的称谓而做出的误解或夸张。
那么,为什么史书会将“周方伯”误称为“西伯”呢?一方面,周人可能为了树立周国在西土的权威,便自我吹嘘,称周代的领袖为“西伯”,以此让外界误以为周国已经掌控了整个西方。另一方面,也有可能是后来的史学家在记录这段历史时,受到周代情况的影响,以周代的称谓来想象过去的历史,进而形成了“西伯”这一称号。最终,周朝取代了商朝,“周方伯”这一头衔被神化为“西伯”,并且流传下来。
从这些历史事件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,历史的叙述往往是经过胜利者的加工与演绎的,姬昌从“周方伯”到“西伯”的称谓,正是历史书写者对周朝盛大历史的再创造与塑造。
发布于:天津市中国股票配资网,配资一流股票配资门户,在线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